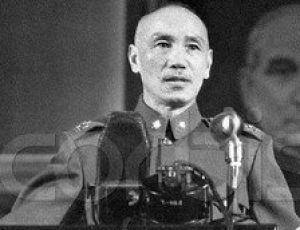说起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,诸多启蒙先驱中,有一对兄弟功不可没,他们就是周氏兄弟——鲁迅(原名周树人)及其二弟周作人。鲁迅,自不必在此赘述,上过初中的人,对他已是非常熟悉。而周作人呢,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他生前的最后二十年,在文坛上是寂寞的,而且辞世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,他的作品更几乎被人们所遗忘,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现代散文开山大师(《中国新文学史》)的地位。
 鲁迅之弟周作人:现代散文开山大师
鲁迅之弟周作人:现代散文开山大师
一九二○年底,周作人的右肋患了肋膜炎,在日本人开的山本医院治疗数月后仍未痊愈,而人多嘈杂的八道湾又不适于疗养,其兄鲁迅甚是着急,便亲自去西山碧云寺,为他找到休养的房间,有鲁迅的一则日记为证:“二十七日,晴。清晨携二弟往西山碧云寺为二弟整理所租屋,午后回,经海甸(即现在的海淀)停饮,大醉。”
碧云寺位于海淀区香山公园东北角。元代皇庆元年(一三一二年),仁宗皇帝重修香山大永安寺,并更名为“甘露寺”。至顺二年(一三三一年),耶律阿勒弥创建碧云庵。一直到明朝正德十一年(一五一六年),御马监太监于经修缮碧云庵,并改庵为寺。
从一九二一年六月初开始,周作人在碧云寺住了半年,一边疗养,一边潜心研读佛经,还先后写下了《美文》、《碰伤》、《山中杂信》、《一个乡民的死》、《卖汽水的人》等脍炙人口的佳作。此前,周作人是接触过佛经的,而他的日本妻子也是信佛的。此时,他潜心研读佛经,固然有消遣的缘故,但内心有苦闷,也是确实的。刚搬入碧云寺不久给好友孙伏园写的《山中杂信》,便似乎有佛的声音,隐隐地,像缓缓的闷雷,在字里行间响动着。查鲁迅的日记,可以证明周作人在这段时间读的经书确实不少。
“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,取回《佛本行经》二本。”(一九二一年四月二日)
“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,带回《出曜经》一部六本。”(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二日)
“下午往山本医院视二弟,持回《起世经》二本,《四阿舍暮抄解》一本。”(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)
“午后往山本病(似乎应为医)院视二弟,持回《楼炭经》一部。”(一九二一年四月三十日)
“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,持回《当来变经》等一册。”(一九二一年五月十日)
“下午往卧佛寺购佛书三种,二弟所要。”(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)
“下午至卧佛寺为二弟购佛经三种,又自购楞伽经论等四种共八册……”(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八日)
“上午为山本医院为潘企莘译。往卧佛寺为二弟购《梵网经疏》、《立世阿毘昙论》各一部。”(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)
“午后往山本医院,晚得二弟信并《大乘论》二部。”(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七日)
周作人研究佛经,在一些文章里也经常引用佛理,如《山中杂信》、《胜业》、《吃菜》、《入厕读书》、《谈戒律》、《释子与儒生》等。但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至他去世的二十多年里,在他的文章里再也难觅与佛有关的片言只字。这其中缘故,可能与他晚年对现实的顿悟有关罢。
寻访周作人当年在碧云寺的住处,很是费了一番周折,因为惟一的线索就是他给友人的书信及公开发表的文章。他在《山中杂信》中写道:“近日天气渐热,到山里来往的人也渐多了。对面的那三间房,已于前日租去,大约日内就有人搬来。般若(音bōrě)堂两旁的厢房,本是“十方堂”,这块大木牌还挂在我的门口。但现在都已租给人住,以后有游方僧人来,除了请到罗汉堂去打坐以外,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挂单了。”
在《入厕读书》中写道:“……民国十年我在西山养过半年病,住在碧云寺的十方堂里,各处走动,不见略略像样的厕所……”
令我遗憾的是,寻遍整个碧云寺,也不曾见有般若堂和十方堂的所在;寺里的工作人员似乎大都没听见过这两个名字,有的可能都不清楚是哪几个字,更遑论给我指点了。还好,文中提到的罗汉堂倒是有一个,可是里面陈列着的据说是清代的五百余尊木质罗汉雕像,也没法告诉我什么。里面一位工作人员虽也不知般若堂和十方堂在何处,但他肯定地告诉我,碧云寺曾经历过几次大劫难,有的地方遭毁重建后,可能旧名儿就不用了。他还说,以前寺里允许住人的也就是前面的两个院子,一个是东边的含青斋,一个是西边的禅堂院。我与他道了谢,走出罗汉堂,穿过院子东角门,前面豁然见有一个院子。前门口挂一牌儿,上书“禅堂院,建于明代,为僧人修行处,一七四八年乾隆重修碧云寺,钦题‘鹫光合印’匾,二○○六年新辟《千年香山》历史文化展。”
再看周作人《一个乡民的死》的记述:“我住着的房屋后面,广阔的院子中间,有一座罗汉堂……”,他在《山中杂信》中还写道:“般若堂里早晚都有和尚做功课,但我觉得并不烦扰,而且于我似乎还有一种清醒的力量,清早和黄昏时候的清澈的磬声,仿佛催促我们无所信仰、无所归依的人,拣定一条道路精进向前。”字里行间,冒出那么多冷静的咏叹,仿佛他一时间得到了仙风道骨,多了一些佛道之气。同时,也可以由此断定,周作人当年在碧云寺的疗养所在,就在如今的禅堂院:正中是第二展室,东西厢房分别是第一、第三展室,但他究竟住哪一间已经不重要了。
拍了几张照片后,我步出院门,信步从大雄宝殿西侧到御碑亭。碑亭之北有两块石碑,四面都刻着乾隆御制的律诗和绝句。几百年的风雨侵蚀,石碑上面的字迹许多已经模糊,但隐约可认出“香山适才游白社,越岭便以(似乎是乾隆已的笔误)至碧云”,“玉泉十丈瀑,谁识此其源”等。乾隆是太有诗才了,据说写了上万首诗,堪称写诗者之最,要是现在,那他得挣多少稿费呀。可惜,遗憾的是,贵为九五之尊的他,没有一首诗使他迈入诗人的门槛。周作人除了专门写《乾隆的恶诗》,嘲讽这位自称为十全老人的弘历不通诗文,还在《山中杂信》中挖苦他“实在是旧诗的难做,怪不得皇帝”,“倘若他生在此刻,抛了七绝五律不做,专做较为自由的新体诗,即便做的不好,也总不至于被人认为‘哥罐闻焉嫂棒伤’的蓝本罢。”
除了御碑亭是周作人疗养时经常散步的地方,还有其东侧的水泉院,他也经常涉足。水泉院因院内“卓锡泉”而得名,依就山势,叠筑山石,亭台池桥,峭壁如城,泉清石美,林深径幽。院内数十株柏树从几丈高的绝壁石缝间生长,盘根错节,宛如长在城墙上的柏林,很是好看,为大自然鬼斧神工倾倒之时,我又不得不感叹生命之顽强。泉水自岩壁间涌出,发出潺潺之水流声,一路流出院外。院里还有著名的三代树,也堪称一绝。据文献记载:该树“生于枯树间,初为槐,历数百年而枯;在根中复生柏,又历数百年而枯;更生一银杏,今已参天矣。”此树龄已有三百余年,在树根四周,仍清晰可见枯死的柏树桩。
真可谓:一树三生独得天,知名知事不知年,问君谁与伴晨夕,只有山腰汩汩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