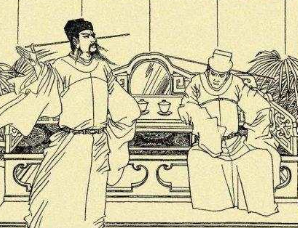一即位就接手了一个烂摊子
宋神宗即位时,大宋开国已历百年。但他继位的第三天,三司使韩绛就奏报:自仁宗朝宋夏战争以来,征调财力,动用国库,“百年之积,惟存空簿”。神宗这才知道自己继承的是怎样一副烂摊子。说起来很难令人相信,在大宋建国的第一个世纪,增长最快的居然是——军队。宋太祖时,全国军队只有20余万,结果到仁宗朝已经增加到120多万,神宗继位时,仍然有116万之多,足足增加了5倍有余,成为当时全世界当之无愧的(人数)第一大军,放到1000年后居然也能排到前四。
 宋神宗赵顼接手的是怎样的烂摊子
宋神宗赵顼接手的是怎样的烂摊子
以当时的人口来负担如此巨大的军队开支,其困难可想而知。宋仁宗皇佑年间任过三司使的蔡襄,曾对当时的军费开支作过统计:按禁军每人50千、厢军每人30千计算,军队开支总额达4800多万,占全部财政收入的5/6,简直令人难以想象!难怪刚刚继位的神宗无法理解这一“积贫”现象,直呼:“穷吾国者,兵也!” 另一方面,宋军人数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加强对外敌(辽和西夏)的防御,以及大量招募流民为军(以避免他们造反)。但日益庞大的人数换不来战斗力,以致“盗贼攻之而不能御,戎狄掠之而不能抗”。宋军在与辽、西夏的边境冲突中,仍旧败多胜少,竟致泱泱大国赂奉夷狄以换取边疆无事,令人气短;是为“积弱”。
“尽复唐之故疆”
在不过20岁正是血气方刚年纪的宋神宗看来,这样“积贫积弱”的局面是不可容忍的。他求治心切,对当时的元老大臣寄予很大的期望。即位次年,他召见前宰相富弼,问以边事,早已在对夏战争失败中磨尽了棱角的富弼答曰:“须是二十年不说着用兵二字。”再问治道,回答是“安内为先”。而老夫子司马光所能提供的治国忠告也只有“官人、信赏、必罚”六个字,实为老生常谈,说了等于没说。
如此回答大不合新天子的心意。另一位元老大臣韩琦日后就总结,神宗的志向是,“聚财积谷,寓兵于民,则可以鞭笞四夷,尽复唐之故疆”。
太祖赵匡胤的统一雄心
实际上,宋朝的建立,彻底扭转了唐代“安史之乱”之后东亚大陆政治版图的碎片化趋势。就连当时的各割据政权也看到了赵匡胤的统一雄心,后蜀宰相李昊就对其主说:“臣观宋氏启运,不类(后)汉、(后)周,天厌乱久矣,一统海内,其在此乎。”但宋代从未完成将东亚大陆重新整合为一体的目标:虽然比较顺利地兼并了南方的荆南、后蜀、南汉、南唐与吴越,却在幽州(今北京)惨败于契丹人的铁骑,被迫放弃了“华夷一统”的梦想,承认契丹(辽)是对等的兄弟之国,并不甘心接受宋辽二元并存的天下秩序格局。
但在汴梁朝廷看来,契丹只是一个例外,“蛮、夷、戎、狄,舍耶律氏则皆爵命而羁縻之。有不臣者,中国耻焉”。对于地处“汉唐旧疆”之内的周边政权,更被视为宋廷“恢复”的对象。这些地方主要包括,名义上是“静海军”的“大越”李朝(今越南北部);法理上是“定难节度使”,却公然反宋自立的“河西李氏”(即西夏);孤悬河西走廊一隅的“归义军”(后被西夏吞并)、在唐代后期逐步被吐蕃占领的河湟地区(“武威之南……皆故汉郡县”)以及念兹在兹的契丹占领下的“燕云十六州”,虽然与契丹约和后,表面上“中国之人遂以燕为外物,不置议论之内”。至于原是汉代郡县却在唐代自立的南诏(大理),“艺祖(太祖)皇帝鉴唐之祸,乃弃越牂诸郡,以大渡河为界,欲寇不能,欲臣不得”,后世宋帝遂也不将其列入“汉唐旧疆”之内。
“富国”只是手段,“强兵”才是目的
可以说从变法伊始,王安石与宋神宗之间就有着分歧。
这位年轻气盛的宋神宗,“知祖宗志吞幽蓟、灵武,而数败兵,帝愤然将雪数世之耻”。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是,在宋神宗即位之初,新皇帝亲自为宋仁宗时期著名将领狄青题写了祭文,以表彰其“在仁宗时,奋于戎马间,捍西戎连取奇功”的卓越战绩。这在武人地位卑下的宋代实在异乎寻常,显示出神宗一改之前“真宗、仁宗意在无为,一用至柔,凡外敌慢侮、请求,无不可忍”,决心“用武开边,复中国旧地,以成盖世之功”的态度。也正因宋神宗有开边之意,“己而擢用王介甫(安石),首以用兵等说称上旨,君臣相得甚欢”。对于宋神宗而言,由王安石主导的一系列改革旨在“富国强兵”,而其中 “富国”与“强兵”相比较,“富国”只是手段,“强兵”才是目的。反观王安石,“自翰林以来,未尝一日言及于用兵”,似乎对外用兵并不是他的兴趣所在。
 宋神宗赵顼
宋神宗赵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