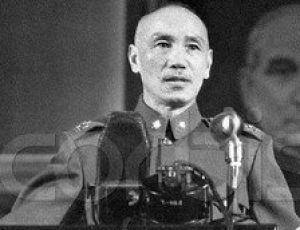假如今天有人不知道莎士比亚,不管他属于哪个国家,那让我们先鄙视一下,他一定是个没读过书的人,需要脑补。在群星闪耀的世界文学天空,莎士比亚是一颗巨星。我们这一代的阅读史,就是一个戴着意识形态眼镜的批判史,但在我的记忆中,即使在前苏联号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莎士比亚,即使在文革中将全部世界文学都打倒的时候,也没有人写过文章批判莎士比亚。
 为什么托尔斯泰看不起莎士比亚
为什么托尔斯泰看不起莎士比亚
然而,有一个作家就敢站出来狠批莎士比亚,他就是托尔斯泰,世界文学星图上另一颗耀眼的巨星。也只有他有这个资格,把莎士比亚贬得一钱不值。在他75岁高龄写的一篇文章中,他直言莎士比亚的剧作毫无是处,琐碎浅薄,东拉西扯。莎士比亚的思想是混乱的,人物性格是不连贯的,情节是不合逻辑的,人物语言也不是实际生活中的语言。总之,莎士比亚既没有刻划人物性格的能力,也没有写对白的能力。
最让托尔斯泰鄙夷的是,莎士比亚对人生采取的是看透一切的态度,没有值得一提的思想或信念,不讲道德和世界观,将不公正的社会等级视作天经地义。托尔斯泰搞不明白,为什么全世界有那么多人喜欢莎士比亚?他得出的结论是,全世界人都被欺骗了!
托尔斯泰是个关心社会的人,所以他批评莎士比亚不关心社会问题,但他的此番言论却遭到英国作家奥威尔的反驳。如所周知,写出《1984》的奥威尔是一个更加关心政治的作家,唯其如此,他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,应当比托斯泰理解得更准确。奥威尔承认,按照托尔斯泰自身的逻辑,他的批评是有道理的,莎士比亚的确不讲情节的一贯性,他的人物就像大多数英国人,“虽然有行为准则却没有世界观”。
奥威尔这句话深刻表明了英国人的性格与其政治文明的关系,他觉得没有世界观的英国人没有什么不好。正如英国学者赫斯勒特所言:“我们都是哈姆莱特。”但这种性格却成了托尔斯泰最反感莎士比亚的地方,作为俄罗斯精神的代表,他强调世界观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,而莎士比亚却总是对一切都兴致盎然,在托尔斯泰眼里,这是“一种对实际生活过程感到谈不上愉快而只是兴趣的倾向”。言下之意,莎士比亚不可能写出生活的本来面目。从他们的分歧中,我们可以看出英国与俄国采取的不同的历史道路。
这里还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,什么是伟大文学作品的标准?
托尔斯泰采用的文学标准是真诚和真实,厌恶庸俗,这也是他那个时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道德标准。比如,在《伊里奇之死》中,伊里奇这个人物就活得不真实,所以他痛苦,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。而在英国人看来,自然就是真实。如诗人约翰生称,莎士比亚是独一无二的自然诗人,是共同人性的真正儿女,他认识到有节制的情欲会导致幸福,而过度的情欲会导致灾难,其人物都是受这些具有普遍的感情和原则影响的结果,这些感情和原则能够震动各种人的心灵。
另一位性格接近盎格鲁理性的德国大诗人歌德也说,他只想和莎士比亚生活在一起,莎士比亚是个美妙的万花筒,没有比他的人物更自然的了,他写的是“自然的真实”。的确,莎士比亚对生活多样化的同情,恰恰是出于高贵的情怀。他的剧作并非没有中心主题,如《麦克白》写野心,《奥赛罗》写嫉妒,《李尔王》写权欲和背叛,《哈姆莱特》写思想与行动的关系。
换言之,莎士比亚的剧作表现的都是普遍的人性,如慷慨或贪婪、英勇或怯懦、诚实或狡狯、节制或野心。就此而言,一个读过并思考过莎士比亚作品的人,不会庸俗到哪里去。
这个颇有意思的争议其实也显示了时代的价值观念变化,莎士比亚时代的幸福、美德、力量、智慧等价值标准,随着浪漫主义潮流的兴起,变成了动机、真诚和心灵纯洁,由此造成了文学观念的变化。如果说,莎士比亚是通过快乐来告诉世人什么是真善美,而托尔斯泰则不是这样,他是俄罗斯的弥赛亚情节与西欧的浪漫主义的结合,要通过痛苦来告诫世人什么是真善美。
自从席勒提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之后,文学家就可以大致分成两类。按照以赛亚·伯林的说法,一种文学家是只对一个中心思想感兴趣的刺猬,另一种文学家是对所有事物都感兴趣的狐狸。托尔斯泰是前者,莎士比亚则是后者。用歌德的话说,莎士比亚告诉人们:“我们称之为恶的东西,只是善的另外一个面,对善的存在是不可缺少的,与之构成一个整体,如同热带要炎热,拉伯兰要上冻,以致产生了一个温暖的地带一样。”
波兰哲学家科拉科夫斯基有一个更明晰的划分,他认为欧洲观念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维模式,一种是牧师思维,认为事物背后存在着一个终极原因;另一种是弄臣思维,对一切终极原则都表示怀疑。托尔斯泰是牧师,莎士比亚则是弄臣。在经历了牧师的绝对思维控制之后,弄臣的怀疑与反讽曾成为前东欧的文学主流。而在西欧,后现代作品表现得同样是终极价值世界崩塌后的自我嘲讽。
也许,在对存在的根本看法上,世界文学正在从托尔斯泰回归莎士比亚。
由此看来,哈姆莱特的犹豫就不是性格上的弱点了,既不是歌德所说:“一件伟大的事业担负在一个不能胜任的人的身上”,也不是柯勒律治所说,过多的“精力全花费在作决定上,反而失却了行动的力量”,而是哈姆莱特面对一个人类的永恒问题产生了怀疑:我们称之为恶的东西,是否只是善的另外一面,对善的存在不可缺少?
记得少年时读到田汉的话剧,其中一个人物引用了哈姆莱特的名言:To be or not to be,that’s the question。心里就有一种震动,隐约感到其中包含了生命中的全部疑问和选择。后来读到朱生豪的译本,这句话翻译成“生存还是毁灭,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”。显然,朱先生只是译出了这句话的部分意思。这个翻译例子不过是再次表明了莎士比亚这句话的真确性:一百个观众就有一百个哈姆莱特。
今天,我们当然不会再像莎士比亚那样去看待人类、社会与政治,对待托尔斯泰也是一样。但是,他们对人性的弱点都有着深刻理解,同时对人类抱有希望。如果不是表现了永恒的人类问题,他们的作品不可能常存于世。
为此,我们必须既向莎士比亚致敬,同时也要向托尔斯泰致敬。